

电影大师伯格曼一生拍了50多部电影,最神秘也最复杂的一部,大概是《假面》。
他自己说,“《假面》和《呼喊与细语》是我的极限。”

学者戴锦华也说,《假面》是她相对看得比较少的一部,“因为精神施暴,肉体施暴和社会的暴力,都被伯格曼最强烈地用在了这部影片当中。”
影片讲述了两个女人的故事:
女演员伊丽莎白,在一次拍摄中突然不说话了。一个叫做艾尔玛的年轻护士被雇来照料她。
从医院到海边别墅,艾尔玛为了诱使伊丽莎白开口,甚至讲出了自己最隐秘的私事,并渐渐有了麻烦……

影片的灵感来自伯格曼一次长达数月的住院。
“住在医院里,一个人会产生一种灵魂出窍、幻游太虚的强烈感受”。
在这之前,他刚刚从毕比·安德森那里结识了丽芙·乌尔曼,两个演员面貌上的相似让他很吃惊,心里已经暗暗决定要为她们做个剧本。
还有一次,他偶然看到剧组的两位女演员伸出各自的手在阳光下比较,这一场景使伯格曼深深着迷,立即决定要从它生发出一部作品来,这就是《假面》。
《假面》始于一片漆黑。
然后是光点,弧光灯,字幕,快速掠过的追逐镜头、勃起的阳物、钉进手掌心的钉子、女演员和台前的脚灯,还有电视中越南和尚的自焚画面以及死去女人的侧影和白布覆盖着的小男孩,接下来是一个男孩从病床上爬起来……
观众甚至来不及判断它们是否相关。

在那个男孩的前面,出现了一片微弱的、无法解释的模糊痕迹,逐渐增强、清晰,成为一张漂亮女人的脸。
他抚摸它犹如触碰一张银幕,一幅肖像或是一面镜子。
“我们所经历的现实,”伯格曼后来曾说,“事实上如同梦境一般荒唐、恐怖和逼人。”
影片结束时,又是那个男孩再次试探性的触摸巨大模糊的女人的脸,然后剪接到弧光灯,灯光渐熄。
《假面》的原文是persona,也可以翻成“人格”。
“这要追溯到欧洲文化的源头上。”在Lens的讲座上,戴锦华分享道,“最早那个‘人格’,并不像我们今天理解的是内在的,刚好相反,是外在的。就是你要通过戴一个面具,才能成人,才有了人的位置,或者说人格的形成。”

舞者在《假面》海报下
某种意义上,“表演是带着面具体验他人,或假装另一个自己。表演是给出独一表情,让面具与自我融为一体……”
在Lens举办的“魔灯犹在——伯格曼和他影响的时尚与艺术”展览上,侯莹舞蹈剧场带来了一场向《假面》致敬的表演。
演出之前,侯莹和编导汪圆清,带着几个舞者来Lens空间看场地,“我就发现这个空间有语言、有分量,有它的庄严感、肃穆感。”

Lens空间里,舞者们身着常服混在观众间,演出不经意地开始……(摄影:陈诗悦)
他们就想把空间完全关闭起来,让舞者和观众用身体语言去互动。
观众可能会感觉到一点点压迫或者冲突,自然或者不自然地被舞者带动,也会迸发丰富的情绪、感受。
“真正美妙的时刻是在你们即将被接触,还没有被接触到,又在等待着。我已经看到了有些眼神都在闪烁着紧张着,走向我了,走向我了……”

零距离的互动交流,利用整个空间完成一次无法复制的表演(摄影:陈诗悦)
“戏剧也好,舞蹈也好,艺术也好,其实无非是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对我们的内心、对周遭的环境,对一切有了更加敏感的感知。”
“我们带着莫名,又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时候很期待他们来,但是突然有人手过来了你又不知道干什么,但是还要表现得很镇定……”

而在空间的二楼,没有参与进去的、沉默的旁观者,就像看电影一样,在看着空间里所有人的状态流动。
“在生活中你们是健谈的,但到了剧场以后你们变成了不说话的人。你们期望对方发生什么,对方给你什么,这个状态就非常像《假面》中病人伊丽莎白的状态。阿尔玛是一个护士,反倒变成了一个演员,因为那个病人在沉默,她在不断地调动自己的情绪,讨好也罢,迎合也罢。她就变了角色,从一个护士变成了一个被观察者。”编导汪圆清说,他们想用舞蹈回应《假面》中的这种张力。

演出前,侯莹还带了一个美国的艺术节总监来看伯格曼的展览。那个人在瑞典生活了很多年,现在家人还在那边。
她感觉,在瑞典,大家还有一点不太愿意去碰触伯格曼,因为伯格曼谈到的话题是所有人不愿意碰触的,大家会有一点点把他隔开的感觉,她对中国能够有这样一个展览,能够对戏剧的心理、对人生有比较不掩饰的讨论,感觉到意外而兴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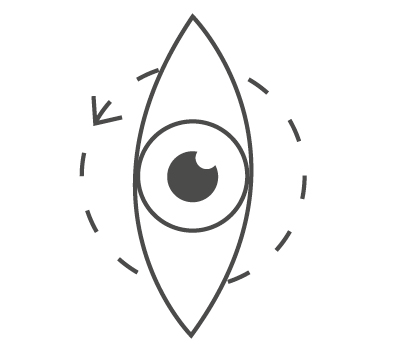




Next \




视频和文字版权为“Lens·重逢岛”所有
部分舞蹈图片由侯莹舞蹈剧场提供
如需转载,请联系后台